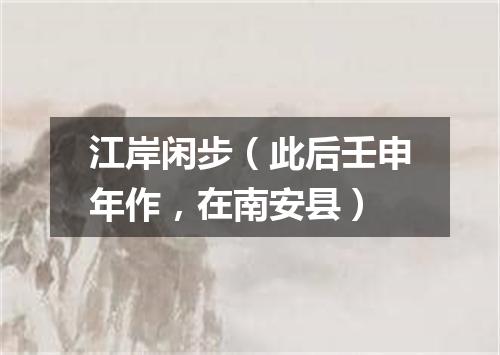
一手携书一杖筇,出门何处觅情通。
立谈禅客传心印,坐睡渔师著背蓬。
青布旗夸千日酒,白头浪吼半江风。
淮阴市里人相见,尽道途穷未必穷。
江岸闲步(此后壬申年作,在南安县)
一手携书一杖筇,
出门何处觅情通。
立谈禅客传心印,
坐睡渔师著背蓬。
青布旗夸千日酒,
白头浪吼半江风。
淮阴市里人相见,
尽道途穷未必穷。
译文:
一手提着书籍,一杖拄着竹筒,
走出门口想寻找知己的方向。
与禅师站立交谈传递心灵的印记,
与渔夫坐倦倚背部的蓬篷。
青色的帆布上夸耀着酒的浓香,
白发的人头之间半江的风咆哮。
在淮阴市的人们互相相遇,
纷纷表示在路途穷困未必无所得。
诗意:
这首诗描绘了作者韩偓在南安县江岸闲步时的情景。他提着一手的书籍,拄着一杖竹筒,走出家门寻找心灵的交流与找到志同道合人的方向。他与禅师聊天,传递了心灵的印记,与渔夫坐在一起休息,躺在背部的蓬篷上。诗中还描绘了青色的帆布夸赞着酒的美味,白发的人头间吹过咆哮的江风。最后,作者所在的淮阴市的人们告诉他即使路途困难,也未必一无所得。
赏析:
这首诗通过描绘诗人闲步江岸的场景,表达了对知己的渴望和对心灵交流的向往。诗中禅客与诗人站立传递心灵的印记,渔夫躺在蓬篷上休息,都显示了作者对安静、自由、与自然亲近的追求。韩偓在诗中也借助青布帆和白头浪的形象,把自然景物与人生境遇相结合,以此表达了人生的艰辛和执着追求的意义。最后一句“尽道途穷未必穷”揭示了人生困难不等同于无法获得成功,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整体而言,这首诗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揭示了他对真挚友谊和善良的人性的推崇。同时,通过描绘丰富的自然和人生的景物,诗人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宁静、富有哲思的心灵享受。
jiāng àn xián bù cǐ hòu rén shēn nián zuò, zài nán ān xiàn
江岸闲步(此后壬申年作,在南安县)
yī shǒu xié shū yī zhàng qióng, chū mén hé chǔ mì qíng tōng.
一手携书一杖筇,出门何处觅情通。
lì tán chán kè chuán xīn yìn,
立谈禅客传心印,
zuò shuì yú shī zhe bèi péng.
坐睡渔师著背蓬。
qīng bù qí kuā qiān rì jiǔ, bái tóu làng hǒu bàn jiāng fēng.
青布旗夸千日酒,白头浪吼半江风。
huái yīn shì lǐ rén xiāng jiàn, jǐn dào tú qióng wèi bì qióng.
淮阴市里人相见,尽道途穷未必穷。
韩偓(公元842年~公元923年)。中国唐代诗人。乳名冬郎,字致光,号致尧,晚年又号玉山樵人。陕西万年县(今樊川)人。自幼聪明好学,10岁时,曾即席赋诗送其姨夫李商隐,令满座皆惊,李商隐称赞其诗是“雏凤清于老凤声”。龙纪元年(889年),韩偓中进士,初在河中镇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入朝历任左拾遗、左谏议大夫、度支副使、翰林学士。
光化三年(900年),宦官头子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发动宫廷政变,废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韩偓协助宰相崔胤平定叛乱,迎昭宗复位,成为功臣之一,任中书舍人,深得昭宗器重,多次欲立为相,都被力辞。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李继昭依附宦官头子韩全诲,排挤崔胤,崔胤召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入朝,意欲抑制宦官集团。李茂贞入朝后,拥兵跋扈,崔胤又想召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入朝牵制李茂贞。韩偓谏道:这样造成“两镇兵斗阙下,朝廷危矣”,应一面罢去李茂贞,一面处理宦官。议尚未行,而李茂贞、韩全诲已将昭宗劫往凤翔。韩偓闻讯,星夜赶往凤翔行在,见昭宗时恸哭失声。昭宗任韩偓为兵部侍郎。后朱全忠兵到,败李茂贞,杀韩全诲,韩偓随同昭宗回长安。
韩偓回长安后,见朱全忠比李茂贞更为骄横,心中甚感不满。一次,朱全忠和崔胤在殿堂上宣布事情,众官都避席起立,只有韩偓端坐不动,称“侍宴无辄立”,因此激怒朱全忠。朱全忠一则恼怒韩偓无礼,再则忌他为昭宗所宠信,参预枢密,恐于己不利,便借故在昭宗面前指斥韩偓。崔胤听信谗言,也不予救护。朱全忠本欲置韩偓于死地,幸经京兆尹郑元规劝阻,被贬为濮州(今山东鄄县、河南濮阳以南地区)司马。不久,又被贬为荣懿(今贵州桐梓县北)尉,再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县)司马。韩偓离京,使昭宗左右无亲信之人。
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弑昭宗,立李柷为昭宣帝(即哀帝)。为收买人心,伪装豁达大度,矫诏召韩偓回京复职。韩偓深知一回长安,即入虎口,便不奉诏,携眷南逃到江西抚州。
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重视延揽人才,派人到抚州邀韩偓入闽。天祐二年(905年)八月,韩偓自赣入闽。
韩偓入闽后,在长汀、沙县寓居一个时期。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改国号梁,王审知向朱全忠献表纳贡。韩偓对此心有抵触,想再回江西。从沙县走到邵武时,王审知急忙派人前去挽留。但韩偓因感“宦途险恶终难测”,功名之念已淡,坚拒王审知的任命。在从邵武回到沙县后,不久又经尤溪到桃林场(今永春)小住,然后进入泉州。在泉州,受到刺史王审邽父子的优礼接待,住泉州西郊招贤院,多年来疲惫的身心得到憩息。在饱览当地风物之时,又感叹“尽道途穷未必穷”,兴之所至,写下许多有名的诗篇。
不久,韩偓到南安漫游,认为这里是晚年栖止的理想地点,便在葵山(又名黄旗山)山麓的报恩寺旁建房舍,以为定居之地,时称“韩寓”。在这里,韩偓下地耕种,上山砍柴,自号“玉山樵人”,自称“已分病身抛印绶,不嫌门巷似渔樵”,过着退隐生活。梁龙德三年(923年),韩偓病逝,威武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傅实为其营葬,墓在葵山之阳。
韩偓才华横溢,是晚唐著名诗人,被尊为“一代诗宗”。其诗作大体上可分3个时期:初期是在被贬谪之前;中期是在贬谪之后,入闽之前;晚期在入闽后,特别是在泉州、南安定居之后。初期在朝为官,深得昭宗信任,仕途上春风得意,生活上优渥奢华,所作诗多是艳词丽句,正如后来他在南安寓所整理《香奁集》的序文上所述:“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充满缠绵浪漫的色彩。不过,也有些清新可诵的诗句,如脍炙人口的“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燕子不来花着雨,春风应自怨黄昏”等。被斥逐出长安后,韩偓屡经转徙,目击乱离,诗风有很大转变,多半叙写个人坎坷遭遇,倾吐胸中悲愤之情,诅咒战乱,同情人民。入闽之初,韩偓行踪未定,过尤溪时,正值泉州王氏军与南汉军激战后,村落成墟,写出传诵千古的名句:“水自潺湲日自斜,屋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只见花。”到泉州、南安定居后,写出“中华地向城边尽,南国云从海上来;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和《咏荔枝》等富有地方色彩的诗篇。晚年,热爱定居后的樵耕生活,写了“此地三年偶寄家,枳篱茅屋共桑麻”,“病起乍尝新桔柚,秋深初换旧衣裳”等诗句,抒发闲适心情。韩偓诗作,以入闽后的作品最多。尽管后人称韩偓为“香奁体”的创始人,其实,现实主义乃是韩偓诗作的主流。其诗集《玉山樵人集》,曾由《四部丛刊》重印传世;《全唐诗》收录其诗280多首。
韩偓诗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诗篇。它们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衰而亡的图景。作者喜欢用近体尤其是七律的形式写时事,纪事与述怀相结合,用典工切,有沉郁顿挫的风味,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寓于清丽芊绵的词章,悲而能婉,柔中带刚。他的作品多写上层政治变乱,触及民生疾苦者较少。而艺术上缺乏杜甫沉雄阔大的笔力和李商隐精深微妙的构思,有时不免流于平浅纤弱。
韩偓的写景抒情诗构思新巧,笔触细腻。而最大的特色,还在于从景物画面中融入身世之感,即景抒情,浑涵无迹。七律《惜花》写得悲咽沉痛,被人视作暗寓亡国之恨。一些写景小诗如《醉著》、《野塘》,以白描手法勾摹物象,构图明晰,设色疏淡,宛如一幅幅饱含诗意的水墨画卷。至于反映农村乱败景象的《自沙县抵尤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寓时事于写景之中,更有画笔与史笔相结合之妙。
韩偓作《香奁集》写男女之情,风格纤巧。对此历来评价不一。今有明汲古阁刻本《韩内翰别集》1卷,附补遗1卷。另《香奁集》有元刊3卷本和《汲古阁》1卷本传世。
据《宣和书谱》记载,韩偓虽不以字誉当世,但行书写的极好,曾有《仆射帖》、《艺兰帖》、《手简十一帖》等传世,宋明之人认为他的字“八法俱备,淳劲可爱”。
韩偓诗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诗篇。它们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衰而亡的图景。作者喜欢用近体尤其是七律的形式写时事,纪事与述怀相结合,用典工切,有沉郁顿挫的风味,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寓于清丽芊绵的词章,悲而能婉,柔中带刚。他的作品多写上层政治变乱,触及民生疾苦者较少。而艺术上缺乏杜甫沉雄阔大的笔力和李商隐精深微妙的构思,有时不免流于平浅纤弱。
韩偓的写景抒情诗构思新巧,笔触细腻。而最大的特色,还在于从景物画面中融入身世之感,即景抒情,浑涵无迹。七律《惜花》写得悲咽沉痛,被人视作暗寓亡国之恨。一些写景小诗如《醉著》、《野塘》,以白描手法勾摹物象,构图明晰,设色疏淡,宛如一幅幅饱含诗意的水墨画卷。至于反映农村乱败景象的《自沙县抵尤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寓时事于写景之中,更有画笔与史笔相结合之妙。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韩偓纪事:“偓小字冬郎,义山云:尝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句有老成之风。因有诗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偓,字致尧,今曰致光,误矣。”
(韩偓作《香奁集》写男女之情,风格纤巧。对此历来评价不一。今有明汲古阁刻本《韩内翰别集》1卷,附补遗1卷。另《香奁集》有元刊3卷本和汲古阁1卷本传世。)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余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余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
据沈括《梦溪笔谈》——《香奁集》应为和凝所著。
细绎有关诗文可见,韩偓与道教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与唐代其他诗人一样,韩偓和道士也有着一些交往,见诸姓名的有钱氏道士、孙仁本、吴颠等。先看钱氏道士,韩偓有诗《花时与钱尊师同醉因成二十字》云:“酒仙同避世,何用厌长沙?”在大好春光里,他与钱氏道士同饮共醉,并且共称为“酒仙”,可见二人十分投机。再看孙仁本道士,“齿如冰雪发如黳,几百年来醉如泥。不共世人争得失,卧床前有上天梯”(《赠孙仁本尊师》),或许正是他不争得失的态度和品格,引起了韩偓的共鸣。对于吴颠道士,韩偓更是推重,在《赠吴颠尊师》中说他“未识心相许,开襟语便诚”,并且愿意拜吴颠为兄长。另外,韩偓和一些隐居江湖的处士如崔江、李思齐等多有交往。从《赠易卜崔江处士》和《赠湖南李思齐处士》可见二人也都是细心研习道法的。 另外,韩偓与道教的关系还可以从以下几点窥见一斑:
对道教经典的熟识。韩偓对《南华真经》和《黄庭经》最为熟悉和喜爱,所谓“赖有南华养不材”(《驿步》)、“一卷黄庭在手中”(《使风》)。韩偓多次提及《南华真经》(即《庄子》),《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云“调鼎何曾用不材”、《深村》云“甘向深村固不材”以及“赖有南华养不材”(《驿步》)皆是取自《庄子·山木》。《访虞部李郎中》“更觉襟怀得丧齐”、《凄凄》“深将宠辱齐”、《小隐》“灵椿朝菌由来事,却笑庄生始欲齐”则可见作者接受了庄子“齐物”的思想。《过临淮故里》“荣盛几何流落久,遣人襟抱薄浮生”,“浮生”来源自《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访明公大德》云“各自心中有醴泉”,“醴泉”则用《庄子·秋水》鵷鶵“非醴泉不饮”事。《余寓汀州沙县……或冀其感悟也》云“子牟欢忭促行期”,则是借《庄子·让王》中子牟事反其意而用之。
亲自参加道教修炼。韩偓曾经亲自参加道教“辟谷”的修炼,《赠湖南李思齐处士》云“知余绝粒窥仙事,许到名山看药炉”,《秋村》云“绝粒看经香一柱,心知无事即长生”。所谓“绝粒”就是“辟谷”、不食谷物,是道教重要修炼方法之一。韩偓参加道教呼吸修炼,《十月七日早起作时气疾初愈》诗云“阳精欲出阴精落,天地包含紫气中”,就是在黎明时候,阳气初生,阴气衰落,此时练功者进行服气修炼、吐故纳新,以达到以气攻病、祛病强身的效果。韩偓的修炼应该主要是精神修炼、内丹术,韩偓的“息机”、“遗虑”、“去物欲,简尘事”正是道教注重“存思通神”、“离境坐忘”的精神修炼,《使风》提到的《黄庭经》便是注重“内丹”的上清派尊奉的最为重要经典之一。因为晚唐五代由于更多的人认识到服食丹药的荒谬和危害,外丹逐步衰落,注重“精、气、神”修炼的内丹逐步兴盛。但对于外丹韩偓应该也是熟悉的,如《赠湖南李思齐处士》中提到“许到名山看药炉”,《寄邻庄道侣》云“药窗谁伴醉开颜”,可见邻庄的道侣也是炼丹药的,《蜻蜓》中也提到“云母”的意象。
对道人隐逸的推崇和神仙生活的向往。从前面韩偓与道教、处士的交往就可以看出他对隐逸的兴趣,既有孙仁本的“不共世人争得失”的赞扬,也有对崔江“门传组绶身能退”的钦佩。更能直接表现这种心态的是《送人弃官入道》,对朋友的弃官入道韩偓是持热烈支持的态度的,他有感于“社稷俄如缀”,认为“忸怩非壮志,摆脱是良图”,最后寄语朋友“他日如拔斋,为我指清都”。韩偓对神仙生活同样充满了向往,对道教壶中神仙境界的更是有着好奇,“壶中日月将何用?借与闲人试一窥”(《赠易卜崔江处士》)。《漫作二首》其一写道“丹宵能几级,何必待乘槎”,登上丹宵的仙境,并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也未必要乘槎于海。《仙山》云“一炷心香洞府开”,作者谓心中虔诚能感通神仙,如焚香一样。《梦仙》一诗更直接而深刻表明了他的道教信仰,诗中先描写紫宵云阕的美景,然后嗟叹阮肇从仙境归来太快、对张骞乘槎天河深表羡慕。诗的最后说“澡练纯阳功力在,此心惟有玉皇知”,表达自己对修道成仙的真诚与渴望。
对道教的自我认同。韩偓任翰林学士时就曾经“鹤帔星冠羽客装”(《朝退书怀》),完全是一副道士形象。韩偓有《寄邻庄道侣》一诗,称自己的朋友或伙伴为“道侣”,这正是道教徒彼此之间的称谓。《寄禅师》云“他心明与此心同,妙用忘言理暗通”,意思是说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是相通的;细绎其诗味,在这里韩偓把禅师作为佛家的代表,而把自己作为道教的代表。可见,韩偓对道教有着某种自我认同感。
从韩偓对佛教态度看其对道教的态度。韩偓也有大量与佛教相关的诗歌,他曾多次造访寺庙,与佛教徒也有着较多的交往。《游江南水陆禅院》比较显明地显示了韩偓对佛教的态度“早于喧杂是深仇,犹恐行藏坠俗流。高寺懒为携酒去,名山长恨送人游。关河见月空垂泪,风雨看花欲白头。除去祖师心法外,浮生何处不堪愁”。从这里可以看出,韩偓很早就不喜欢佛教的繁杂喧闹,甚至连一些寺庙也懒得去游玩,只是佛教的“心法”多契合诗人的情怀。《即目》其二亦云“动非求进静非禅”,明确表明自己“动”并不是要干禄求进,“静”也并非要学佛修禅。《寄禅师》中则以道教道家自居。可见,韩偓对佛教“心法”虽然比较欣赏,但他并不倾心于此。韩偓对道教比对佛教有更多的亲近感。